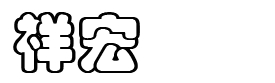“长安三伏苦午热,日赤尘红气酷烈。闲曹谢客不出门,汲水瓷缸贮清冽。平头摇扇尚流汗,一卷横看肱欲折。”
这首诗乃是清代大学者王鸿绪所作,名曰《三伏叹》,讲的便是旧京之热。老北京的夏天,热起来尽管赶不上四大火炉,但也能把人难过得够呛。在那个既无空调、又无电扇的时代,人们揣摩出了许多奇思好办法,在体内体外发明出了清凉迷人的“小气候”,仅仅今日现已不为人知。
清代诗人冯溥在《佳山堂诗集》中有云:“赤乌扇火散云涛,六月凌阴价倍高。争说冰寒能救喝,十钱买得似葡萄。”冰寒救喝,指的大约是冰核,《都门琐记》中说“夏天沿街卖冰核,铜盏声磕磕然”,即指此物。
冰核跟现如今的冰棍相同,纵能含嚼解热也是一时顷刻,并且中医不主张在暑时暴饮暴食严寒之物,以其伤脾胃害元气,所以真正为旧京大众喜爱和广泛承受的“避暑正解”乃是“暑汤”。据《京都习俗志》记载,此物乃是用“煎苏叶、藿叶、甘草”等熬制成汤,于街头巷尾免费给顶着酷日过路的人们饮用。
到了民国时期,暑汤的“规制”加强完善,其丹方多是选用合适伏天服用的香薰汤、双花汤等,并加以改进,具有祛暑散热、清三焦火、理气宽中等成效。那年月,做买卖跟做人相同,存了“善良”之心才干发家致富,所以老字号在慈善事业上谁也不甘人后。据北京风俗学者张善培先生回想:鹤年堂、同仁堂、庆仁堂等等,以及一些巨贾大户,夏至一过就在自家门面、药王庙、关帝庙和富贵热烈的路口摆张长条桌,上面放着装满“暑汤”的大玻璃缸或木桶,以及瓷碗、玻璃杯,过路者能够留步恣意饮用,既解渴又祛暑。当然,这种暑汤只能是现场饮用,管够,但是要想给家里人带是不行的,只能买药店专门配好的药剂包,拿回家自己煎制。有一些药铺也布施一些装有藿香正气丸的小药包,上面一般印有店肆的字号以及“暑天防热,珍重身体”的字样,既是善举,又能起到宣扬自己的作用老北京的生意人,那可真是惠人助己两不耽搁。
广义的暑汤,还包含绿豆汤。照理说,煮绿豆汤无非是绿豆煮水,撒以白糖,冰镇冷饮,本钱和制造程序远逊于酸梅汤和西瓜汁,但老北京的王公府第,对绿豆汤的推重远胜于后两者。大略是由于中医对绿豆汤抑火祛暑之效愈加推重,这也从另一个旁边面阐明,古人很早就了解在健康饮食上“只选对的,不选贵的”的道理。
北京文明学者胡金兆先生回想,他打记事儿起(上个世纪三十时代),“每到夏天,在琉璃厂海王村公园外的路口,就有一个白油漆的木架子,架着一口缸,架子上有几个用细铁链拴着的小搪瓷杯,缸内是绿豆汤,免费供过往的拉车的、卖苦力的解渴解暑。”这些绿豆汤由琉璃厂各大商户轮番值勤担任供给。一般是上午一次,下午一次,“这是厨房大师傅的活儿,利用饭口的空地,大锅熬绿豆汤,用两个铅铁桶挑着送去倒进缸中,由热而凉,等不到全凉,也就喝光了”。
在琉璃厂,免费供给暑汤的不止这一处。其时西琉璃厂商务印书馆对面路北、东琉璃厂姚江会馆前,都设有暑汤点。商家们遵从的是与人为善、不能为富不仁的主意,只需商业昌盛、铺户许多的当地,大多有此组织供给。有的当地比琉璃厂做得还要好,比方前门大街东西的各条街内都有暑汤供给处。供给暑汤的木架子上“用细链子拴着的搪瓷缸,从没见过谁把它拧断拿走”。
有些人说起“老北京”,形象之一是夏天喜爱光膀子,其实这仅仅个别现象,就笔者小时分在南城日子的阅历,绝大部分北京爷们儿哪怕到了太阳最毒的时分也仍是穿戴跨栏背心的,当然那背心十有八九现已破得好几个窟窿了,偶然有位大爷光着膀子,也是啪啦啪啦地用大蒲扇拍着肚子和胸脯,并没有不文明的感觉,气候热,谁都能了解。
但在没有跨栏背心的年月,一到伏天,考究换上浏阳圆丝细麻布做的麻布褂。据风俗学大师金受申先生回想:这种麻布熨得板平,穿在身上非常清凉。麻布又分红两种,一种名叫“沙塘月色”,为老年人的衣料,另一种名叫“月白色”,是妇女及四十岁以上人的衣料。还有门布和葛布,这两种布尽管粗糙,但未经漂白,所以坚韧性强于麻布,且价格比麻布低价,更合适低收入集体运用,做长衫短褂均无不行,是老大众过夏天的首要衣料。在线织和麻纱织的背心还没有传入北京之前,人们夏天考究穿“汗络”,便是把布剪成胸前背面两块,在腋下和膀子处有接缝处,每隔寸许用绳子联合,不只清凉并且透风,较现在的背心愈加舒适。
夏装就图个凉快简便,相比之下,手里摇的扇子考究可就多了去了,尤其是纨子弟手里用的折扇,说是送风之用,其实不啻是一把艺术品。风俗学家邓云乡先生在校园读书时,一到快放暑假,总要跑到南店去买两个扇面:“那些洒金的、发笺的价钱都贵,我买的一般是杭州舒莲记五层锦料,即用五层绵纸裱在一起的。”买到后找一些闻名的文人学者在扇面上作画题字,再买个湘妃竹、凤眼竹的扇骨子,请店员用篾钎把扇面穿骨子的当地挑开穿好,再切齐两头糊在大骨子上,一把新扇子就做好了,“这些精巧的扇面,也能够叫作美术工艺品,真是叫人拍案叫绝的”。
不过,在老北京最具代表性的仍是芭蕉扇,许多人认为这扇子是芭蕉叶所制,其实是一种误解,这种扇子是用蒲葵的叶子做的,所以正确的说法应该叫大蒲扇。大蒲扇一般是一尺巨细,价格实惠公正并且扇起来风大凉快,不管从哪个视点讲都极为“亲民”。现在只需有关于老北京的习俗画,往往会看到这样的画面:老爷爷或老奶奶拿着一把大蒲扇,给坐在板凳上、用双手杵着下巴的小朋友讲故事,丰子恺还画过一幅画,一个小娃娃把两个大蒲扇夹在胯下当车骑这样的场景笔者幼年还有形象。小时分,夏天,在姥爷家门口那棵枝繁叶茂的老槐树下,姥爷坐在藤椅上,一边摇着大蒲扇给我扇风,一边给我讲三国演义的故事,开裂的大蒲扇上缠着白色胶布,摇起来啪啦啪啦作响,伴着树上一刻也不停歇的蝉鸣,阳光透过层层叠叠的树叶洒在地上,就连影子也有浓浓的绿意。
作家关庚在《我的上世纪》里回想,在北京还没有救火队的时分,每个家庭为了防火,都预备有水枪,“是铜制的,用的时分,把水枪的一头浸入水中,上下移动套筒,水就从上嘴喷出来,几下就能够喷一桶水”。这样的水枪在夏天有一共同的用途,那便是许多家庭在盛暑时节,都用它喷洒宅院用来降温。
别的一件“空调”则是当代人肯定想不到的,那便是鱼缸。一说起老北京的旧日日子,人人皆知“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那鱼缸并不如人们幻想的都是瓷缸,其实大多便是木质的大桶,还有口大底尖的沙缸,相对来说最好的是陶泥缸,由于其透气又不易漏水,合适鱼日子。夏天假使宅院里有这么几口大鱼缸,加上天棚和覆满绿叶的葫芦架,会构成一个阴凉湿润的“小气候”,待在里边非常舒适。
当然,还有必不行少的竹帘和冷布。老北京的窗户,一般都是“上纸下玻璃”,即上边为木格纸窗,下边是大块玻璃,窗户纸用的均是高丽纸,夏天一到,屋子里逐渐炽热,所以各屋就都扯去熏黄了的旧窗纸,糊上了新的冷布。冷布是一种稀少纱,通风又能防蚊蝇入室,多染成绿色,这样看起来如在绿荫中,给人以清凉之感。糊完了冷布,再做卷窗,这种卷窗离地较高,卷时用长约一米的木棍,上面嵌以齿状长方木,上下推进即可将窗卷起。卷窗的作用是在冷布通风的基础上,避免住在屋里的人乍受夜寒,所以其更多的是为了“保温”。不能不说老年间的人们在过日子上别有一番精心,难怪夏仁虎在《旧京琐记》里赞许曰:“京城屋制之美备甲于四方,以研讨数百年,因地因时,皆有格式也。”
还有竹帘,挂在屋门上,也是起通风防蚊蝇之作用,还有一番作用是,不管身处室内仍是室外,隔着竹帘观看都有模糊的美感。竹帘的制造说来简略,但考究起来也不得了,比方清宫的竹帘,那是由内务府主管帘子库的御用工匠制造的,帘子库的地址设在地安门内黄华门胡同,用料和工艺都用尽精巧之能事。至于民间,说是竹帘,有的就爽性是在冷布的下面加一木棍以坠重,挂在门上。笔者小时分更多见的是拿挂历纸搓成圆棍后用胶黏起,再用线穿成的帘子,常常穿过的时分都像落雨相同哗啦啦地响。
老北京给室内“制冷”的办法,还有一种,今已不为人知,那便是用冰镇茉莉花熏香。小贩们清晨负着长方竹筐,内置小铜匣多具,用碎冰块镇于周围,匣内窨白玉兰及茉莉花朵,还有散朵晚香玉及玉簪花窨于湿袋,买者带回家或置于室内,或挂于襟上,嗅那丝丝凉意的花香,顿觉提神醒脑。而在室外,爱美的北京人栽种的夹竹桃、百日红、小珊瑚、菖蒲莲等等,也有动人肺腑之用,翁偶虹先生回想旧时暑夜:“每当新月初上,置竹榻凉簟于庭中,偃卧其上,俯视银河,月色高寒,花香暗袭,蒲扇停挥,清凉无汗。”那种意境,真是夸姣。